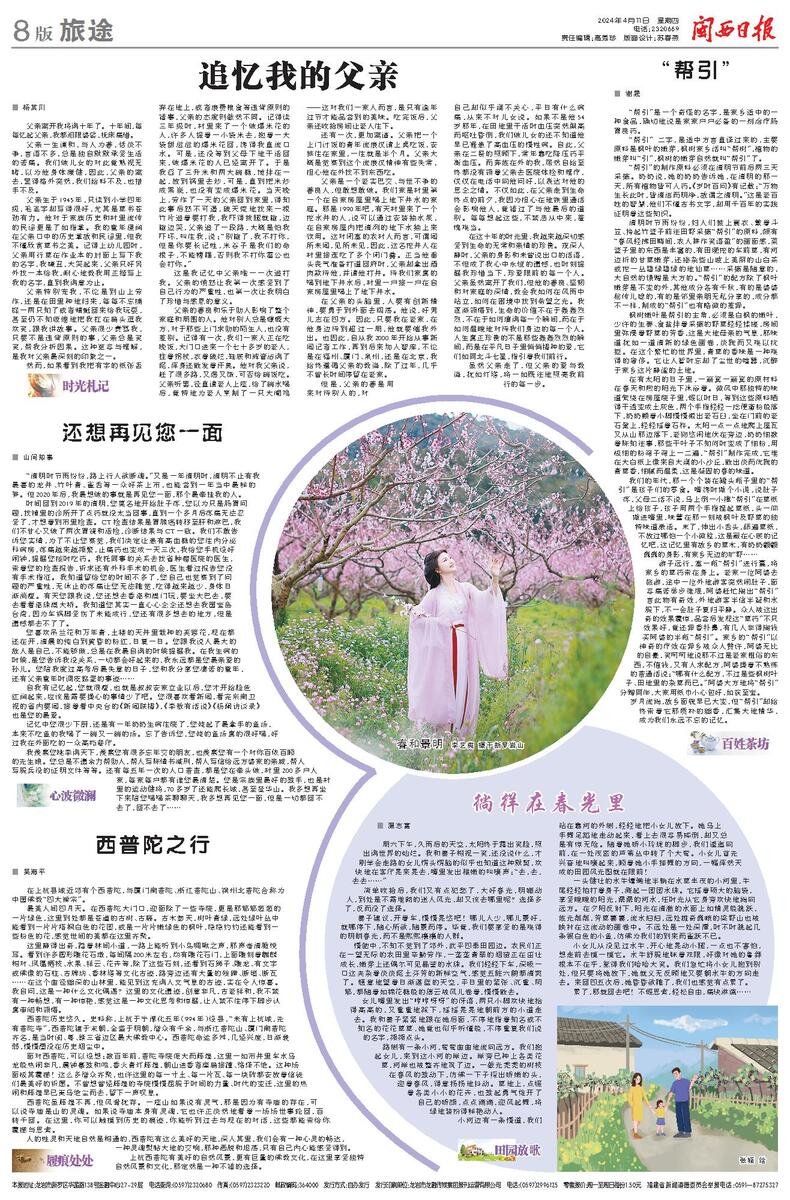- 放大
- 缩小
- 默认
追忆我的父亲
■ 杨其川
父亲离开我将满十年了。十年间,每每忆起父亲,我都泪眼婆娑,抚床痛惜。
父亲一生谦和,与人为善,恬淡不争,言语不多,总是独自默默承受生活的苦痛。我们做儿女的对此竟熟视无睹,以为他身体康健,因此,父亲的离去,显得格外突然,我们始料不及,也措手不及。
父亲生于1945年,只读到小学四年级,毛笔字却写得很好,尤其是草书苍劲有力。他对于家族历史和村里流传的民谣更是了如指掌。我的童年浸润在父亲口中的历史掌故和民谣里,但我不懂欣赏草书之美。记得上幼儿园时,父亲用行草在作业本的封面上写下我的名字,我嫌丑,大哭起来,父亲只好另外找一本给我,耐心地教我用正楷写上我的名字,直到我满意为止。
父亲特别宠我,不论是到山上劳作,还是在田里种地归来,每每不忘捕捉一两只知了或者蜻蜓回来给我玩耍,甚至仍不知疲倦地把我扛在肩头逗我欢笑,跟我讲故事。父亲很少责骂我,只要不是违背原则的事,父亲总是笑笑,帮我分析因果。这种宽容与理解,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之一。
然而,如果看到我把有字的纸张丢弃在地上,或者浪费粮食等违背原则的错事,父亲的态度则截然不同。记得读三年级时,村里来了一个做爆米花的人,许多人提着一小袋米去,抱着一大袋甜滋滋的爆米花回,馋得我直流口水。可是,还没等到父母下地干活回来,做爆米花的人已经离开了。于是我舀了三升米和两大碗糖,搅拌在一起,放到锅里去炒,可是,直到把米炒成黑炭,也没有变成爆米花。当天晚上,劳作了一天的父亲回到家里,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,破天荒地找来一根竹片追着要打我,我吓得拔腿就跑,边跑边哭,父亲追了一段路,大概是怕我吓坏,叫住我,说:“别跑了,我不打你,但是你要长记性,米谷子是我们的命根子,不能糟蹋,否则我不打你雷公也会打你。”
这是我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追打我。父亲的愤怒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性,也第一次让我明白了珍惜与感恩的意义。
父亲的善良和乐于助人影响了整个家庭和周围的人。他对别人总是慷慨大方,对于那些上门求助的陌生人,也没有差别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,大门口进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,拄着拐杖,衣着破烂,鞋底和裤管沾满了泥,浑身还散发着汗臭。他对我父亲说,赶了很多路,又渴又饿,可否给碗饭吃。父亲听罢,径直请老人上座,给了碗水喝后,竟特地为老人烹制了一只大阉鸡——这对我们一家人而言,是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品尝到的美味。吃完饭后,父亲还收拾房间让老人住下。
还有一次,更加离谱。父亲把一个上门讨饭的青年流浪汉请上桌吃饭,安排住在家里,一住就是半个月。父亲大概是觉察到这个流浪汉精神有些失常,担心他在外找不到东西吃。
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、与世不争的善良人,但敢想敢做。我们家是村里第一个在自家房屋里喝上地下井水的家庭。那是1990年吧,有天村里来了一个挖水井的人,说可以通过安装抽水泵,在自家房屋内把清冽的地下水抽上来饮用。这对闭塞的农村人而言,可谓闻所未闻,见所未见,因此,这名挖井人在村里接连吃了多个闭门羹。正当他垂头丧气准备打道回府时,父亲却拿出酒肉款待他,并请他打井。待我们家真的喝到地下井水后,村里一户接一户在自家房屋里喝上了地下井水。
在父亲的头脑里,人要有创新精神,要勇于到外面去闯荡。他说,好男儿志在四方。因此,只要我在老家,在他身边待到超过一周,他就要催我外出。也因此,自从我2000年开始从事新闻记者工作,再到后来加入智库,不论是在福州、厦门、泉州,还是在北京,我始终遵循父亲的教诲,除了过年,几乎不曾长时间停留在老家。
但是,父亲的善是用来对待别人的,对自己却似乎漠不关心,平日有什么病痛,从来不对儿女说。如果不是他54岁那年,在田地里干活时血压突然飙高而呕吐昏倒,我们做儿女的还不知道他早已罹患了高血压的慢性病。自此,父亲在二哥的照顾下,常年靠吃降压药平衡血压。而奔波在外的我,居然自始至终都没有领着父亲去医院体检和理疗,仅仅在电话中向他问好,以表达对他的思念之情。不仅如此,在父亲走到生命终点的前夕,我因为担心在地铁里通话会影响他人,竟错过了与他最后的道别。每每想起这些,不禁悲从中来,羞愧难当。
在这十年的时光里,我越来越深切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亲情的珍贵。夜深人静时,父亲的身影和未曾说出口的话语,不但成了我心中永恒的遗憾,也时刻提醒我珍惜当下,珍爱眼前的每一个人。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,但他的善良、坚韧和对家庭的深情,教会我如何在风雨中站立,如何在困境中找到希望之光。我逐渐领悟到,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轰轰烈烈,不在于如何填满每一个瞬间,而在于如何温暖地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人生真正珍贵的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瞬间,而是在平凡日子里悄悄播种的爱,它们如同北斗七星,指引着我们前行。
虽然父亲走了,但父亲的爱与教诲,犹如灯塔,将一如既往地照亮我前行的每一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