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放大
- 缩小
- 默认
我在乡间有亩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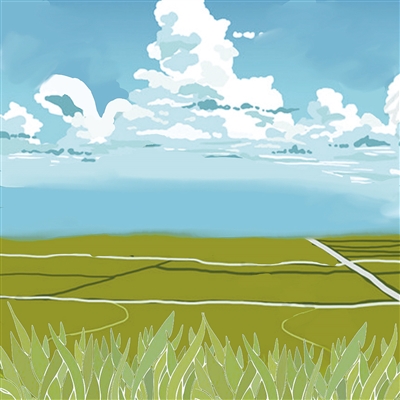
陈玲蓉 绘
■ 张文琼
一弯钩月还挂在西边的天空,繁星依旧在那里闪烁,我和母亲打着赤脚朝着自家要割稻子的那亩田走去。一路上,我还睡意未消,脚踩在窄窄软软的田埂上,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母亲后面。母亲一边数落着我晚上不应该看小说到深夜才睡,一边唠叨着近十几天该干的“双抢”农活。
下了稻田,我站着弯腰,右手捏牢刀柄,左手抓住稻根稍上部位,从右往左,靠左手下面稻根部位割去。一次割6丛,向前一步,再割6丛,刚好一把,放至边上稻堆。不到半小时,我就感到腰酸背痛,一个早上下来,手指也被割破了好几道,汗水渗进去,一阵阵钻心的痛。
那是1989年的暑假,我刚初中毕业。父亲到苏邦煤矿下井挖煤,农忙“双抢”也没回家,于是割稻、打稻、插秧等这些农活,就落到母亲和我身上,妹妹则负责晒谷子、做家务。那么炎热的天气,那么繁重的“双抢”活,却没有一个强的“男劳力”,让我们身心疲惫。我哭过多次,赌气不干,向母亲发脾气,甚至欲哭无泪,但活儿还是要干,因为母亲也承受了很大的苦。
当年,我们村一个小组就一台半自动打稻机,大家抓阄轮流用。那天,伯父说,上午他家先用打稻机,下午给我家用。于是,我和母亲上午割完一田的稻子,准备下午来打谷。不料中午时分,乌云密布,狂风大作。我们正在吃午饭,几秒钟内,我和母亲面面相觑,不约而同地扔下手上的饭碗,一起冲向田里。我们要在大雨到来之前把带禾稻子运到晒谷场上用塑料薄膜盖起来,若割下的谷子被雨淋湿,48小时内就会发芽,就不能吃了。
当我挑到最后一担稻把时,倾盆大雨扑面而来。或许是太累了,我挑着被大雨淋湿的稻把艰难走在泥泞的田埂上,脚下一滑,我连忙用双手扶住扁担,保持肩膀上的稻把不掉下来,但没有站稳,一只腿“啪”地跪在地上,另一只腿却还弯曲着。我努力直着腰,挺胸,抓紧肩上的扁担,保持平衡不让稻把掉到地上。这一瞬间的动作是我本能的反应,因为我怕稻子掉到泥土里,母亲会心痛。我想喊不远处的母亲把我扶起来,但喊不出声,心想就这样跪着吧,因为实在太累了。最后母亲看见了,跑过来用肩膀撑着扁担让我站起来,母亲哭了,我也哭了……此后,我努力读书,跳出“农门”,走出了那亩田。
弹指一挥间,三十多年过去了。如今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在“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”的粮食安全政策推动下,这个暑假,我和支部的同志们一起参加“我在乡间有亩田”党员志愿活动,认种了村里的田地。我们卷起裤脚、打着赤脚,站在水田中,手拿秧苗,依着泥线分秧,插秧,一株株秧苗稳稳立在田中,一幅生机盎然的“农耕画卷”徐徐展开。等秋收时,我一定要给朋友送上一袋自己种的粮食,这将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