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山的呼唤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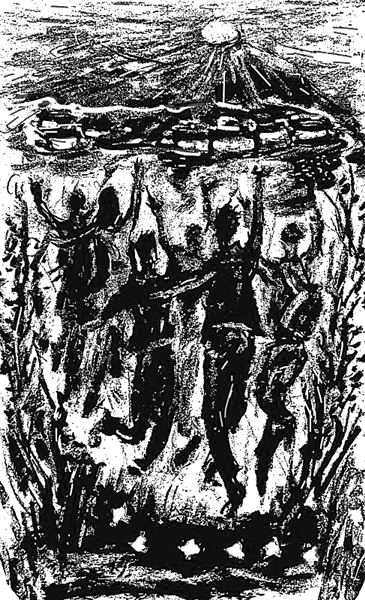
□吴爱华
车子进入下洋境内,车轮下的路沿着山,一路逶迤至深山处。车子在初溪村部停下,一下车,同行文友说,这里好冷啊,气温至少比龙岩市区低5度。冬天寒冷,这是下洋初溪给我的第一印象。我们的目的地是这里的一个自然村——池牛岗。在村里向导的带领下,我们的车子继续向前行进,数分钟后,一座城墙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。下车,目光从城门穿过,“池牛岗”三字醒目于一大石块上。城墙窄,尽地而建,宽约20来米。此处是入池牛岗的必经之路。站在城门外仰看,颇有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气势。从城门步行入内,豁然开朗,一股原生态古寨气息迎面扑来,有农田屋舍;有成群的鸡鸭在田间悠闲觅食;一只大黄狗悠哉悠哉地走在路上;再往里面走去,还可见养蜂人家,更惊艳的是,一只大母鸡带领一群毛茸茸的亲生鸡宝宝在一块空地上觅食,这个久违的亲切画面,只能追溯回我的童年时代。
向导直接把我们带到一家小店铺。在此,早有一精瘦老伯沏好茶候着我们。进去的路上,我们就在揣测这个奇特的地名。“池牛”莫非是宰牛的意思?刚一坐下,我们就急不可耐地向老伯询问“池牛”其义。果然,老伯说,“池牛”就是宰牛的意思。听完他的解释,我会心一笑,用与本地客家话完全同音的汉字“池”来代替,如此大胆、如此有创意的写法,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我想,客家人见了这名字,定能牢牢记住。在闲聊中,我们得知,老伯是当年接头户曾阿石之子。老伯的话匣子随着“池牛岗”的名字而打开,他一边沏茶一边用较缓慢的语速给我们讲“池牛岗”的故事。一百多年前,此地不叫池牛岗,它原来住着胡姓人家。池牛岗人的始祖是个牛贩,早年,始祖从九峰老家赶牛至永定湖坑贩卖,有一天傍晚,行至此,人和牛都已极度困乏,只好在此求住一宿。房东不肯收留,他死活赖着不走。因为,他知道,一天来,人和牛已走了100公里,要是连夜继续赶路的话,人和牛都会累死的。无奈,房东只好道出实情,经常有一帮土匪来此打家劫舍。果然,这一夜土匪又来了。匪首见了群牛和这张生面孔,便问他哪里人氏?他说九峰曾姓人氏。匪首又问,曾某某你可认识?他说,是我叔。匪首说,曾某某是我的故交,我经常到他家,怎没见过你?他说,我常年在外贩牛。就这样,匪首放过了他,并说,晚上就在这里杀牛,犒劳犒劳我的弟兄们,往后,你继续做你的生意,我们不会再为难你的。是夜,他杀了一头牛。从此,每逢湖坑赶集日,他便人和牛一起借宿于此。时间长了,他和房东成了熟人。因那帮土匪经常在这吃吃喝喝的,房东的日子越来越艰难,只好向他借钱维持小日子。时间到了,无力偿还,只能用一间房抵债,而后,又再借,时间到了,又再用一间房抵债。最后,所有房子都变成他的。从此,他就把家安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盆地上,在此开枝散叶。池牛岗就是这么来的,现已有人丁200多号。
讲完故事,老伯带我们参观东盛楼,这是一座土圆楼。看着楼内的新设施,老伯一脸忧伤地叹了口气说:“诶,这么冷清,这是我3个儿子共同出资兴建的,还有外面的城楼与滑梯”。是啊,我们一行人至此已有个把钟头,只见几个从外面进来邀伴一起去喝喜酒的男女,其他再无外人进来。本村大部分人家外迁,只剩老伯在内的几户人家。在这样的空间里,新建的游乐场显得突兀孤独,也因此平添了几分苍凉之感。见此情景,我在心里哀叹,连人影都见不着几个,哪来的生意?
初溪有10座世遗土楼,近年来,随着各地土楼旅游业的兴起,它也顺应历史潮流,有声有色的做起了旅游业,在游客吞吐量较大的一些旅游景点,有不少人在自家门前,摆摊兜售一些土特产和一些小商品,这给部分家庭增加了一些收入。可是,如何让整个村庄获益?这恐怕是横亘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难题。
我的家乡位于经济较发达的高新园区,即便这样,仍旧有不少年青人到经济更发达的城市去打工,更不用说偏远山区的年青人了。
有部叫《一点就到家》的电影,这是一部农村题材的喜剧片,也有人称它为励志片。故事的主人公:有电商梦的魏晋北,有快递梦的彭秀兵,有咖啡梦的李绍群,这3个有梦想,却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年青人,因机缘巧合凑在了一起,在云南一个千年古寨开启创业的故事。一开始,他们经历了不少挫折和失败,后来,他们总结经验把所有外出务工人员召集回寨种植咖啡树,并自主研发成功了一款叫“普洱咖啡”的咖啡。这毕竟是一部电影,编剧和导演赋予了它完美的结局。然而,现实是非常残酷的,无人村随处可见。但,它也给了我们某种启迪,以及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:一个村庄要留住人,必定要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产业链条,并且,要与时俱进,把电商、快递、直播带货等元素融进产业链中。在这部励志片中,我仿佛看到了池牛岗的希望,仿佛看到了千万个村庄的希望,仿佛听到了远山深处的呼唤:年青人,回来吧,家乡需要你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