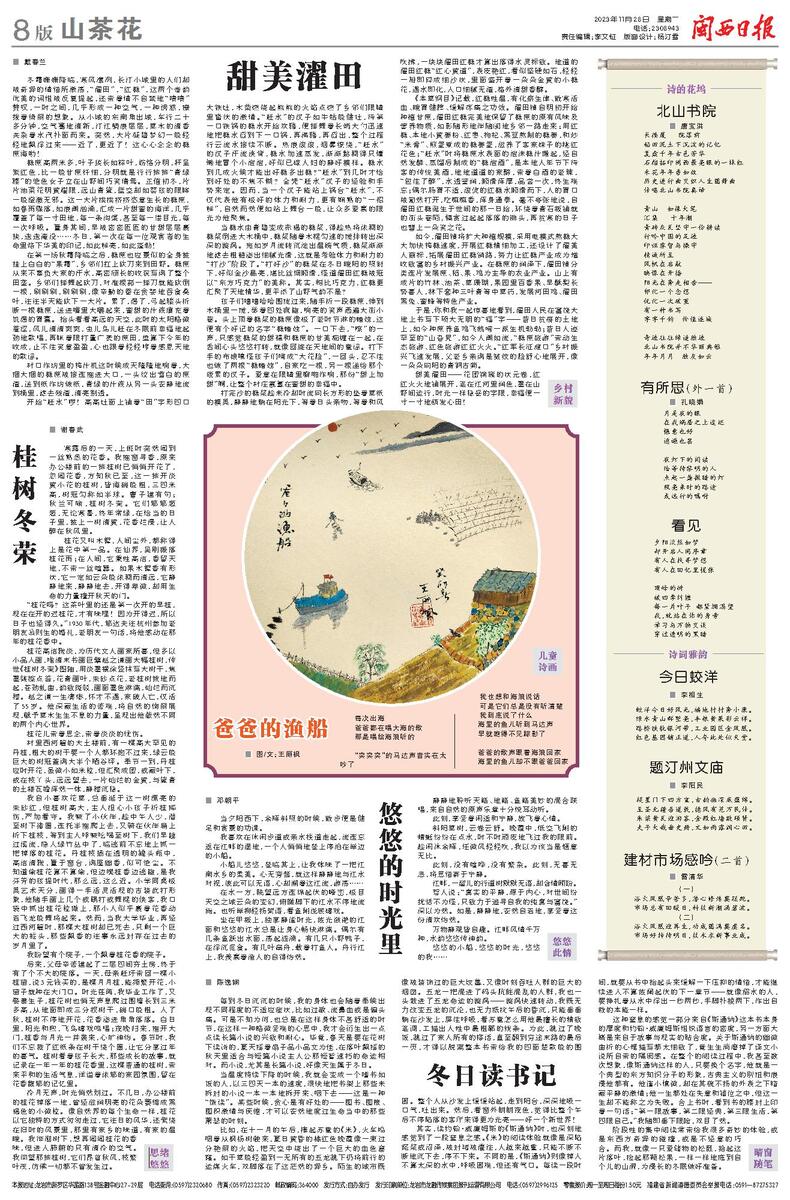冬日读书记
■陈逸娴
每到冬日沉沉的时候,我的身体也会随着季候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应症状,比如过敏、流鼻血或是偏头痛。可是不知为何,也总是在这样身体不甚舒适的时节,在这样一种略微受难的心思中,我才会衍生出一点点读长篇小说的兴致和耐心。毕竟,春天是要在花树下读诗的,夏天摇着扇子品小品文为佳,在落叶飘摇的秋天里适合与短篇小说主人公那短暂速朽的命运相对。而小说,尤其是长篇小说,好像天生属于冬日。
当温度持续下降的时候,我就会变成一个嗜书如饭的人,以三四天一本的速度,很快地把书架上那些未拆封的小说一本一本地拆开来、咽下去——这是一种“饿读”。某些时候,贪心是有好处的——囤书、囤粮、囤积激情与厌倦,才可以安然地度过生命当中的那些萧瑟的时刻。
比如,在十一月的午后,捧起苏童的《米》,火车呜咽着从枫杨树驶来,夏日黄昏的橘红色晚霞像一束过分艳丽的火焰,把天空中烧出了一个巨大的血色窟窿。如干草般轻盈到一无所有的五龙跳下仍将前行的运煤火车,双脚落在了这茫然的异乡。陌生的城市既像被装饰过的巨大坟墓,又像时刻吞吐人群的巨大的烟囱。五龙一把混进了码头肮脏混乱的人群,我也一头栽进了五龙命运的漩涡——漩涡快速转动,我既无力改变五龙的沉沦,也无力抵抗午后的昏沉,只能垂垂躺在沙发上,屏住呼吸,看苏童怎么用他最擅长的精致笔调,工描出人性中最粗鄙的线条。为此,跳过了晚饭,跳过了家人所有的搭话,直至翻到穷途末路的最后一页,才得以脱离整本书带给我的四面楚歌般的围困。整个人从沙发上缓缓站起,走到阳台,深深地吸一口气,吐出来。然后,看窗外朗朗夜色,觉得比整个午后不停陷落的客厅来得更为光亮——好一个新世界!
其实,读约翰·威廉姆斯的《斯通纳》时,也深刻地感觉到了一股窒息之感。《米》的阅读体验就像是深陷泥浆或沼泽,被封堵被灌注,人越来越重,只能不断不断地沉下去,停不下来。不同的是,《斯通纳》则像掉入不算太深的水中,呼吸困难,但还有气口。每读一段时间,就要从书中抬起头来缓解一下压抑的情绪,才能继续进入不算波澜起伏的下一章节——就像溺水的人,要挣扎着从水中浮出一秒两秒,手脚扑棱两下,作出自救的本能一样。
这种窒息的感觉一部分来自《斯通纳》这本书本身的厚度和约翰·威廉姆斯组织语言的密度,另一方面大概是来自于故事与现实的贴合度。关于斯通纳的幽微曲折的心理描写都太细致了,竟生生消磨掉了译文小说所自带的隔阂感。在整个的阅读过程中,我甚至数次想象,像斯通纳这样的人,只要换个名字,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东方知识分子的形象,古典主义的别扭和浪漫他都有。他谨小慎微,却在其貌不扬的外表之下暗藏平静的激情;他一生都处在失意和错位之中,但这一生却不能称之为失败。合上书时,看到书的腰封上印着一句话:“第一眼故事,第二眼经典,第三眼生活,第四眼自己。”我随即垂下眼睑,双目了然。
阶段性的集中阅读常带给我很多奇妙的体验,或是东西方奇异的碰撞,或是不经意的巧合。而我,就像一只爱储物的松鼠,拾起这片落叶,捡起那颗松果,一样一样地拖到自个儿的山洞,为漫长的冬眠做好准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