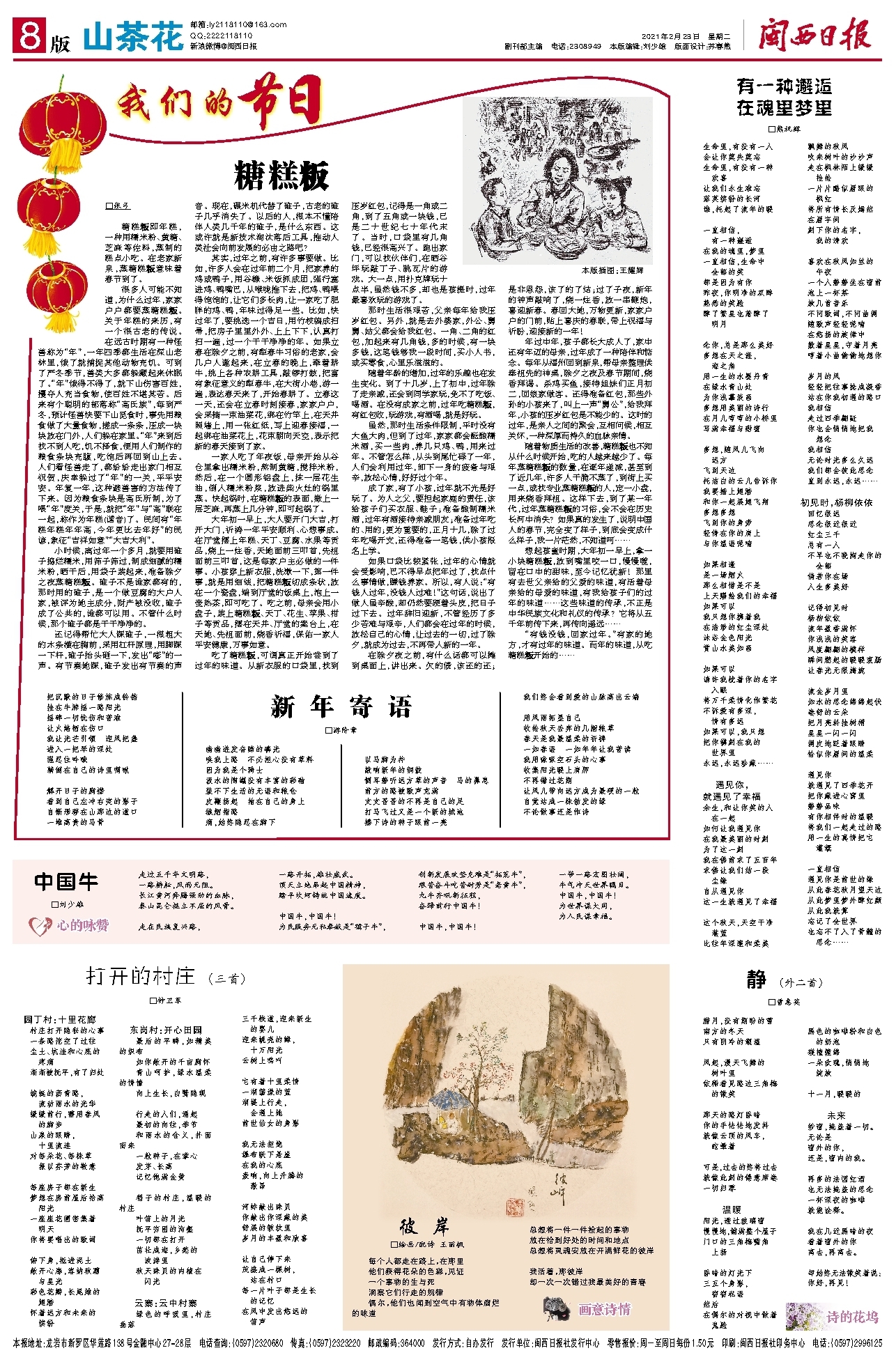糖糕粄

□张弓
糖糕粄即年糕,一种用糯米粉、黄糖、芝麻等佐料,蒸制的糕点小吃。在老家新泉,蒸糖糕粄意味着春节到了。
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为什么过年,家家户户都要蒸糖糕粄。关于年糕的来历,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。在远古时期有一种怪兽称为“年”,一年四季都生活在深山老林里,饿了就捕捉其他动物充饥。可到了严冬季节,兽类大多都躲藏起来休眠了。“年”饿得不得了,就下山伤害百姓,攫夺人充当食物,使百姓不堪其苦。后来有个聪明的部落称“高氏族”,每到严冬,预计怪兽快要下山觅食时,事先用粮食做了大量食物,搓成一条条,压成一块块放在门外,人们躲在家里。“年”来到后找不到人吃,饥不择食,便用人们制作的粮食条块充腹,吃饱后再回到山上去。人们看怪兽走了,都纷纷走出家门相互祝贺,庆幸躲过了“年”的一关,平平安安。年复一年,这种避兽害的方法传了下来。因为粮食条块是高氏所制,为了喂“年”度关,于是,就把“年”与“高”联在一起,称作为年糕(谐音)了。民间有“年糕年糕年年高,今年更比去年好”的民谚,象征“吉祥如意”“大吉大利”。
小时候,离过年一个多月,就要用碓子捣烂糯米,用筛子筛过,制成细腻的糯米粉,晒干后,用袋子装起来,准备除夕之夜蒸糖糕粄。碓子不是谁家都有的,那时用的碓子,是一个做豆腐的大户人家,被评为地主成分,财产被没收,碓子成了公共的,谁都可以用。不管什么时候,那个碓子都是干干净净的。
还记得帮忙大人踩碓子,一根粗大的木条横在胸前,采用杠杆原理,用脚踩一下杆,碓子抬头砸一下,发出“嘭”的一声。有节奏地踩,碓子发出有节奏的声音。现在,碾米机代替了碓子,古老的碓子几乎消失了。以后的人,根本不懂陪伴人类几千年的碓子,是什么东西。这或许就是新技术淘汰落后工具,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吧?
其实,过年之前,有许多事要做。比如,许多人会在过年前二个月,把家养的鸡或鸭子,用谷糠、米饭抓成团,强行塞进鸡、鸭嘴巴,从喉咙推下去,把鸡、鸭喂得饱饱的,让它们多长肉,让一家吃了肥胖的鸡、鸭,年味过得足一些。比如,快过年了,要挑选一个吉日,用竹枝编成扫帚,把房子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,认真打扫一遍,过一个干干净净的年。如果立春在除夕之前,有犁春牛习俗的老家,会几户人邀起来,在立春的晚上,牵着耕牛,挑上各种农耕工具,敲锣打鼓,把富有象征意义的犁春牛,在大街小巷,游一遍,表达春天来了,开始春耕了。立春这一天,还会在立春时刻接春,家家户户,会采摘一束油菜花,绑在竹竿上,在天井照墙上,用一张红纸,写上迎春接福,一起绑在油菜花上,花束朝向天空,表示把新的春天接到了家。
一家人吃了年夜饭,母亲开始从谷仓里拿出糯米粉,熬制黄糖,搅拌米粉,然后,在一个圆形铝盘上,抹一层花生油,倒入糯米粉浆,放进柴火灶的锅里蒸。快起锅时,在糖糕粄的表面,撒上一层芝麻,再蒸上几分钟,即可起锅了。
大年初一早上,大人要开门大吉,打开大门,祈祷一年平安顺利、心想事成。在厅堂摆上年糕、天丁、豆腐、水果等贡品,烧上一炷香,天地面前三叩首,先祖面前三叩首,这是每家户主必做的一件事。小孩穿上新衣服,洗漱一下,第一件事,就是用细线,把糖糕粄切成条状,放在一个瓷盘,端到厅堂的饭桌上,泡上一壶热茶,即可吃了。吃之前,母亲会用小盘子,装上糖糕粄、天丁、花生、苹果、柑子等贡品,摆在天井、厅堂的案台上,在天地、先祖面前,烧香祈福,保佑一家人平安健康,万事如意。
吃了糖糕粄,可谓真正开始尝到了过年的味道。从新衣服的口袋里,找到压岁红包,记得是一角或二角,到了五角或一块钱,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了。当时,口袋里有几角钱,已经很高兴了。跑出家门,可以找伙伴们,在晒谷坪玩敲丁子、跳瓦片的游戏。大一点,用扑克牌玩十点半,虽然钱不多,却也是孩提时,过年最喜欢玩的游戏了。
那时生活很艰苦,父亲每年给我压岁红包。另外,就是去外婆家,外公、舅舅、姑父都会给我红包。一角、二角的红包,加起来有几角钱,多的时候,有一块多钱,这笔钱够我一段时间,买小人书,或买零食,心里乐滋滋的。
随着年龄的增加,过年的乐趣也在发生变化。到了十几岁,上了初中,过年除了走亲戚,还会到同学家玩,免不了吃饭、喝酒。在没有成家之前,过年吃糖糕粄,有红包收,玩游戏,有酒喝,就是好玩。
虽然,那时生活条件限制,平时没有大鱼大肉,但到了过年,家家都会酝酿糯米酒,买一些肉,养几只鸡、鸭,用来过年。不管怎么样,从头到尾忙碌了一年,人们会利用过年,卸下一身的疲惫与艰辛,放松心情,好好过个年。
成了家,有了小孩,过年就不光是好玩了。为人之父,要担起家庭的责任,该给孩子们买衣服、鞋子;准备酿制糯米酒,过年有酒接待亲戚朋友;准备过年吃的、用的;更为重要的,正月十几,除了过年吃喝开支,还得准备一笔钱,供小孩报名上学。
如果口袋比较紧张,过年的心情就会受影响,巴不得早点把年过了,找点什么事情做,赚钱养家。所以,有人说:“有钱人过年,没钱人过难!”这句话,说出了做人虽辛酸,却仍然要硬着头皮,把日子过下去。过年辞旧迎新,不管经历了多少苦难与艰辛,人们都会在过年的时候,放松自己的心情,让过去的一切,过了除夕,就成为过去,不再带入新的一年。
在除夕夜之前,有什么话都可以摊到桌面上,讲出来。欠的债,该还的还;是非恩怨,该了的了结;过了子夜,新年的钟声敲响了,烧一炷香,放一串鞭炮,喜迎新春。春回大地,万物更新,家家户户的门前,贴上喜庆的春联,带上祝福与祈盼,迎接新的一年!
年过中年,孩子都长大成人了,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,过年成了一种陪伴和惦念。每年从福州回到新泉,帮母亲整理供奉祖先的神桌,除夕之夜及春节期间,烧香拜谒。杀鸡买鱼,接待姐妹们正月初二,回娘家做客。还得准备红包,那些外孙的小孩来了,叫上一声“舅公”,给我拜年,小孩的压岁红包是不能少的。这时的过年,是亲人之间的聚会,互相问候,相互关怀,一种深厚而持久的血脉亲情。
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,糖糕粄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吃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每年蒸糖糕粄的数量,在逐年递减,甚至到了近几年,许多人干脆不蒸了,到街上买一点,或找专业蒸糖糕粄的人,定一小盘,用来烧香拜祖。这样下去,到了某一年代,过年蒸糖糕粄的习俗,会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消失?如果真的发生了,说明中国人的春节,完全变了样子,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,我一片茫然,不知道呵……
想起孩童时期,大年初一早上,拿一小块糖糕粄,放到嘴里咬一口,慢慢噬,留在口中的甜味,至今记忆犹新!那里有去世父亲给的父爱的味道,有活着母亲给的母爱的味道,有我给孩子们的过年的味道……这些味道的传承,不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礼仪的传承?它将从五千年前传下来,再传向遥远……
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。”有家的地方,才有过年的味道。而年的味道,从吃糖糕粄开始的……